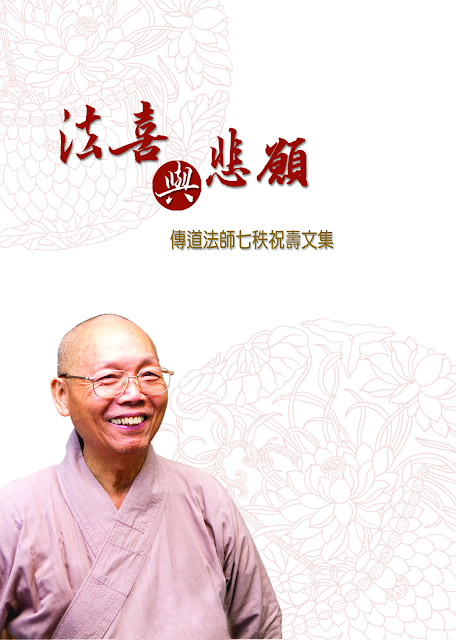在極樂世界永得安寧——哀悼陳啟文老師
陳啟文老師與我同是2007年進入到慈濟大學任教,他在東語系、我在宗教所,因此「同梯」因緣,所以分外與他感覺親切。不只如此,他雖是畢業於國文系,但從事的是思想性研究,指導教授是鼎鼎大名的林安梧老師,既是我的學長、也是我的同仁,再加上他到慈大後轉向佛學研究,因此有更緊密的連結。
印象中他曾跟我說過,他進來慈大教書原是誤會一場,當時的系主任受人之託聘人,基於信任並沒有特別進行面試,結果原先說好要來的轉往他處,啟文老師當時也有申請,被誤以為即此推薦人選而直接進入徵聘流程,經系、院、校三級三審嚴格稽核而完備程序,待到開學後才發現所託非人,此他非彼他,因此上天巧妙安排(美麗錯誤)我們得以成為同事,只能說因緣不可思議!
啟文老師是大家公認的大善人、好好先生,「樂善好施」是眾人對他的印象,對同仁同事總是謙恭有禮,對學生更是照顧有加,深受學生愛載歡迎。聽說他常把自己的存款甚至手機等大方借出,照顧有需要的人,當然也由於跟同學過從甚密,少了師生間分際的拿捏,有時讓自己陷入不必要的紛擾。
啟文老師對於投資尤有心得,他曾表示希望透過投資股票致富,這樣他才能夠捐更多的錢,以「億元男」作為他初步的人生目標。可知他想賺大錢不是為了他自己,而是希望能夠做更多善事、好事。
啟文老師是虔誠的佛教徒,一心歸順阿彌陀佛淨土法門,雖與慈濟人間佛教的修行路數不同,但同懷利他助人之心,所以也沒有隔閡。長年來他的研究論著都是佛學,尤其專攻淨土思想,我們宗教所好幾位學位論文請他來評審,跟我們所亦有頗深緣分。
啟文老師的良善不只對人,還包括對動物,乃至於對幽冥界的眾生。他在花蓮常往墓地跑,甚至在夜間進行烟供施食、引渡亡靈,或許因此緣故,常與陰界眾生打交道,不懷好意的「好朋友」看到了他的良善、找上了他,致使精神出了狀況。
究竟是失智還是卡陰,當有一番科學和宗教的論辯。就科學來說是心智退化的認知障礙,但就宗教而言恐是「異次元」眾生的干擾,冥冥中某種神秘能量牽引著他、困限著他,讓他心神持續惡化。總之這是一個謎,但我相信「敬鬼神而遠之」,不輕易和「他界」有情眾生交通是好的。
啟文老師精神出狀況另一原因,或許也關乎他的家庭關係。他在學校最後數年,聽聞他已經6年沒有見到自己的小孩,原因是娘家對他有所誤解,不喜歡他這個人。然而他又是如此深愛他的妻子和2個孩子,而一個思親心切卻又苦見不到,身心折磨可想而知。雖然清官難斷家務事,但大人的問題終究不該牽累到小孩,長年沒有看到自己親身骨肉,這是何等殘忍,也讓成長中的小孩失去父愛,失去認識、親近良善多才父親的機會,對此我們深感惋惜。
這幾年同輩師友紛紛離去,前年一位慈大通識中心同仁、也是我們宗教所畢業生,亦於五十多歲年紀溘然長逝,讓人深感生命之無常。面對無常,我們毫無招架之力,一方面告訴自己要把握當下,另一方面也提醒自己要淡然放下。
今天(2月19日)是啟文老師的告別式,我因身在花蓮另有課程,僅以此短文表達我對他的深摯悼念,願他一路好走、投生佛國,在西方極樂世界永得安寧!